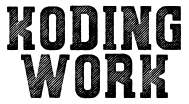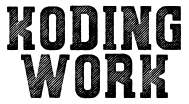「AI 會取代我嗎?」這大概是近幾年來,每個軟體工程師心中或多或少都浮現過的疑問。大家都在討論 AI 將如何取代勞動力,但如果我們只停留在這個問題上,其實就問錯了方向。
在 AI 時代,我們的任務不是被動地使用 AI,而是要反過來思考:如何讓 AI 變得更有效率?
這聽起來可能有點違反直覺,但這背後牽涉到 AI 目前的本質與極限。如果我們不理解這些,直接將 AI 應用在開發流程中,很容易會感到綁手綁腳。這篇文章將從 AI 的基本概念、訓練方法的困境,一路談到軟體工程師在 AI 協作中的新角色與實戰心法。
目錄
揭開大型語言模型 (LLM) 的神秘面紗
首先,我們要理解一件事:至今所有的大型語言模型(LLM),本質上都只是在「模仿」人類的文本與對話。它們最主要的任務,就是預測下一個字 (Token)。
AI 缺乏「世界模型 (World Model)」
LLM 並沒有真正地去「理解」一件事情發生的因果關係。最近 AI 領域的大佬們都在談論一個概念叫做「世界模型 (World Model)」,指的是一種能理解世界運轉原理,並依此進行預測的能力。
舉個例子,我們人類知道「滾燙的熱水壺不能碰,因為會燙傷」,這背後隱含著物理原理。但如果我們只告訴 AI:「看到正在燒的熱水壺,不能碰」,它學到的只是一個指令。當場景換成早餐店裡發燙的鐵板時,它可能就無法舉一反三,因為它不懂那個共通的底層邏輯——「高溫物體會造成傷害」。
Andrej Karpathy(前 Tesla AI 負責人)曾說,我們現在訓練 LLM,不像在培育一個學習中的動物,更像在「召喚一個幽靈 (Ghost)」。動物或小孩會透過與世界的互動、嘗試與犯錯來學習;而現在的 LLM 則是大量吞噬人類的文本,成為我們思想與語言的「分身」,但它本身並沒有真正的思考與理解能力。
當前的訓練方法:為何 AI 會「蒙對答案」?
既然 LLM 有其極限,那為什麼它有時看起來那麼厲害,有時候又幻覺重重?這與它的訓練方式有關。
目前主流的訓練方法,例如監督式微調或強化學習 (Reinforcement Learning),在某種程度上是非常「暴力」的。模型在解決一個問題時,會產生一連串的思考路徑,但我們通常只根據「最終答案」的對錯來給予獎勵或懲罰。
這就像學生時代考選擇題,就算中間的思考過程完全錯誤,只要最後「蒙對」了答案,一樣能得分。這種訓練方式會導致一個問題:模型可能因為錯誤的理由,產生了正確的結果。這也是造成 AI「幻覺 (Hallucination)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一個更理想的方式,是所謂的 Process-based Supervision,也就是像大學申論題一樣,重視整個解題的邏輯與過程,而不僅僅是最終的答案。但這種方式實作起來非常困難:
- 人力評分太慢:讓人類去評估 AI 每一步的思考路徑,成本極高且效率低下。
- AI 評分有風險:讓舊模型(如 GPT-4)去評分新模型(如 GPT-5),新模型很容易找到舊模型的漏洞並產生「對抗樣本」,學會如何「欺騙」評分系統。
一個更聰明的訓練方向:經驗反思 (Experiential Reflection)
既然逐格審查思考路徑如此困難,那還有沒有別條路?最近,來自 Meta AI 等實驗室的研究者提出了一個更接近人類學習方式的方向,稱為經驗反思 (Experiential Reflection) – Agent Learning via Early Experience。
這個概念的核心是將 LLM 視為一個代理人 (Agent)。我們不再只餵給它靜態的文本,而是給它一個任務,讓它在一個真實或模擬的環境中去「嘗試」。
整個流程大致如下:
- 給定任務:例如,「去這個電商網站上買一個東西」。
- 生成行動方案:AI 會生成數十種可能的行動方案(Action),例如「點擊這個按鈕」、「在搜尋框輸入文字」等等。
- 與環境互動:系統會執行這些行動,並從環境中得到真實的回饋 (Feedback),可能是「成功加入購物車」,也可能是「頁面錯誤」。
- 學習因果:最後,模型會根據「問題 + 行動 + 環境回饋」這個完整的數據組來進行再訓練。
透過這個循環,AI 就能慢慢學會「如果我採取了某個行動,大概會發生什麼事」。它不再是單純地模仿文字,而是開始透過試錯來理解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係,這是建構「世界模型」非常關鍵的一步。雖然這個方向仍在積極研究中,但它代表了未來 AI 訓練的一個更理想的典範。
軟體工程師的新角色:成為 AI 的架構師
了解了 LLM 的極限後,我們就能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。我們的價值不再是逐行撰寫樣板程式碼,而是成為 AI 的引導者與架構師。
從高層次來看,我們的任務轉變為:
- 定義系統架構與模組邊界:高層次的架構設計、模組如何切分、介面如何定義,這些是 AI 的弱項,卻是我們的強項。
- 控制複雜度與技術債:AI 看過的文本大多是大型、完善的系統,容易產生「過度設計」的程式碼。我們需要判斷情境,控制實作的複雜度,避免不必要的技術債。
- 確保系統的可維護性與可擴展性:AI 產生的程式碼不一定好維護。我們需要審視其成果,確保整個系統的健康度。
簡單來說,我們負責搭好骨架、劃清邊界,讓 AI 這位超級會寫程式碼的「實習生」去填充血肉。
小心上下文腐爛 (Context Rot)
許多 LLM 號稱擁有超長的上下文視窗(例如 100K Token),但研究與實踐都發現,模型對於上下文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「開頭」與「結尾」,中間的資訊很容易被遺忘。這就是所謂的「上下文腐爛 (Context Rot)」。
如果我們一股腦地把十幾個檔案、上百個函式全部丟給 AI,不僅會迅速消耗寶貴的上下文空間,真正重要的資訊也可能被淹沒在中間而被忽略。
因此我們要理解 Prompt Engineering、Context Engineering,負責把大問題切成幾個明確的小步驟,並在提示詞清楚定義目標、約束、格式,最後給足必要背景,但避免無差別塞一大堆。
實戰分享:我的 AI 協作工作流
在實際開發中,我不會只用一句話叫 AI 寫 Code,而是透過更結構化的方式與它協作。
Case 1:從 API 到前端頁面的開發
在開發一個新功能頁面時,我的習慣是先開一個文字檔,把整個需求從頭到尾定義清楚:
- 定義 API 規格:條列出所有會用到的 API Endpoint,以及 Request/Response 的格式。
- 定義資料傳輸物件 (DTO)。
- 定義前端狀態管理 (State / Store) 的結構。
- 定義 Component 的 Props 與互動行為。
我會將這個脈絡清晰、從上到下的完整說明貼給 AI,讓它一次性生成整個功能的程式碼。這種「頭尾都掐好」的方式,成功率遠高於一句句地下指令。
Case 2:後端 API 的重構與擴充
之前在修改一個後端 API、需要加入新的檢查條件時,我並沒有時間去追溯所有相關的程式碼。我的做法是:
- 提供精準的上下文:我先大致瀏覽了 API 的進入點、呼叫了哪個 Service,然後明確告訴 AI:「請你看這幾個檔案,特別是這個函式。我需要在裡面增加 B 和 C 的檢查。」
- 先 Review 計畫,再實作:我會要求 AI:「先不要動手改,告訴我你打算怎麼改。」它會列出修改計畫,我確認這個計畫符合我們的系統架構,並提出調整建議。
- 迭代與修正:來回幾次,確認命名風格、錯誤訊息都符合需求後,才讓它開始實作。
這個過程,我扮演的角色是提供關鍵資訊的偵探和審核設計圖的架構師,把繁瑣的程式碼閱讀與撰寫交給 AI。
結語
回到最初的問題,AI 不會「取代」我們,但它正在徹底「改變」我們的工作模式。
人類工程師的任務,是透過我們的經驗與智慧,進行系統設計、切分複雜問題、提供精準的上下文,將 AI 的能力最大化。我們不再是單純的「Coder」,而是「AI Coder」,是懂得如何駕馭 AI、讓 AI 為我們高效產出的指揮家。
我們正處於 AI 時代,或者說,AI Agent 十年的第一年,許多訓練方式與應用都還很原始。但可以肯定的是,未來軟體工程師的核心價值,將更多地體現在思考、設計與決策上。